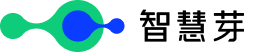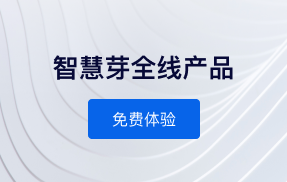点击本文中加粗蓝色字体即可一键直达新药情报库免费查阅文章里提到的药物、机构、靶点、适应症的最新研发进展。
在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研发历程中,经过40多年的努力,该疗法已成为肿瘤学领域的重要治疗手段,然而这一技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约有370多种新型ADC进入临床试验,其中11种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但也有超过150种由于各种原因中止了临床试验。
ADC的毒性问题一直是研发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尽管设计初衷是希望ADC能精准靶向肿瘤细胞,从而有效减少传统化疗带来的副作用,但实际情况是许多ADC依然会带来显著且有时剂量受限的毒性,这些毒性问题主要与其连接子及有效负载有关,而非抗体本身或靶点。
在1980年代,最初的ADC以长春花生物碱和DNA损伤剂为主要成分,1990年代则开始引入卡利奇霉素,随后是auristatin和maytansinoid。而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以烷基并吡唑并嘧啶(PBD)为代表的ADC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喜树碱ADC在临床试验中崭露头角。
关于ADC的耐受性存在一个误区,即通常认为ADC可以扩大治疗窗口,增加最大耐受剂量(MTD)并降低最小有效剂量(MED)。然而,临床数据表明,ADC的耐受性与其相关小分子药物并没有显著差异。尽管某些ADC在接近最大耐受剂量时可以表现出更好的疗效,但这一现象在临床前和临床观察中并不完全一致。
在临床上,与相关的小分子化疗药物相比,ADC在接近MTD时通常表现出更好的疗效。特别是在那些对小分子化疗无效的肿瘤患者中,ADC的应用显示出了显著的治疗效果。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小分子伊立替康和ADC药物sacituzumab govitecan的比较,后者在某些癌症适应症中显示了更高的疗效。
关于ADC的稳定性,尽管理论上提高抗体在循环中的稳定性可以减少药物的游离并提升疗效,但研究表明过度的稳定性可能增加正常组织的毒性。许多已批准的ADC在其链接器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对疗效有益。
另一方面,ADC被称为“魔法子弹”的观点也逐渐被证伪。尽管其设计用于选择性递送药物至癌细胞,实际上抗体结合于肿瘤的比例极低,大部分药物在其他正常组织中被摄取。
最后,ADC领域的未来发展将继续侧重于优化其设计和用途。通过引入新的靶标和药物载体,优化现有药物的分子结构,以及结合其他疗法的组合使用,科学家们期待开发出更有效、更安全的新一代ADC。这些努力旨在解决目前存在的副作用问题,并实现更精准的癌症治疗。
免责声明:新药情报内容编辑团队专注于介绍全球生物医药健康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旨在提供信息交流,不代表任何立场或治疗方案推荐。如需专业医疗建议,请咨询正规医疗机构。